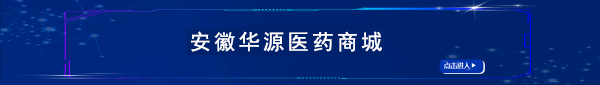2023年10月30日,老牌制药巨头恒瑞,将两款产品授权给国际大药厂默克,拿到1.6亿欧元的首付以及未来可能超过14亿欧元的总交易额。
这项交易,在重新奠定了恒瑞作为“医药一哥”的同时,也给“传统巨头搞创新到底行不行”这份质疑,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。意味着在制药行业,曾经旧王朝里的那些资历、体制、模式等束缚的条条框框,不是完全不能被打破,也能够跟上新生一代的步伐。
在中国,创业容易守业难。尤其是受政策及外部环境影响极高的医药行业,当巨头不容易。
按总市值计算,过去十年医药TOP榜单里,有些走着走着掉出榜单之外再没回来过;有的一直站在榜单里;还有的,曾经离开过,如今又重新回到前排。

图片来源:深蓝观官微
制药行业从来都不是“时间的朋友”。
老技术容易被新机理取代,大品种走下神坛只需要一纸文件,重磅产品很多时候等不到变成“重磅炸弹”的时候,便会迎来价格的内卷。在过去,大多能靠着销售渠道里的规模效应去赚数量上的钱的公司,如今在“压缩中间商”的政策之下,已然覆水难收。
而那些想要保持自己地位的药企们,想去抓住一些荣耀的光环,以及些许名利赋予的在行政以及经营上的特权,也驱动着这一批企业不断去追随时代的脚步,去在座次的名利场里争一个身份。
1、时代里的巨头
其实,回顾中国医药历史,传统巨头们的变迁,与其说是企业自身发展,倒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。
九十年代末,彼时医药行业最需要解决的是“缺医少药”的问题,那时候谁能提供稳定的、有疗效的产品便足以,也催生了一批从零到一敢于去把高校研究成果转化成药品的公司。
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,还属恒瑞。
在彼时相当大比例的中国人还停留在治病靠“三素一汤”(抗生素、维生素、激素和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)治百病的时候,恒瑞是第一家系统性地把肿瘤这个治疗领域作为主攻赛道,靠着一个环磷酰胺完成原始积累。然后引入中国药科大学和医药工业研究院两大外部智囊资源,完成其后面一系列肿瘤和造影产品管线的开发。
当时市场里需求还不是“新的分子、新的机理”,在那个专利和还不是很完善的年代,谁能通过更有效的化学手段把国际上的主流产品成果“复制”出来,就算是一种成功。
除了恒瑞之外,先声、天晴、科伦等巨头们,或多或少都是在某一个其它领域里找到了一套相同的转化模式,然后慢慢成就后期的上位。
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经历:改革开放前后通过个人魅力完成第一桶金的攫取;然后积极拥抱高校资源,成了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第一批吃螃蟹的人;进入21世纪后,在监管层模糊下隐忍着崛起;最终在供给侧改革之后依靠自身的积累享受行业红利。
但是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,药品批文滥竽充数,“招商”和“销售”取代“产品本身”成了行业的核心驱动力。在这样一个“大跃进”的年代,谁能够坚守本心,把成熟&仿制药做到质量稳定、价格亲民,而不是用各种方式去和监管以及支付打游击战,谁就不会卷入到监管俘获中去、因为一些时代的巨幅波动而被淘汰。
那几年的反腐力度可不比今年要小,经常是一个院长后面带出一批医药公司。玩野路子的人多了,监管只能从行业整体上去应对,能做的只有拼命地压价再压价,泥沙俱下,自然给主流公司留不下太多增长的空间。
因此,那段时间,反倒是一批有着稳定原料供给的公司走了出来,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浙江台州原料药产业区的若干家企业:海正、华海、浙江医药等等。一些有自己上游药材种植的中药企业也是如此,比如华润三九、康缘药业。因为有自己的原料供给,在“降价”上显得更从容,同时因为主业范围广,也不会把公司过多的资源和经历放进纯粹的“药品公关”中去。
中药领域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,就是康美。作为一家中药材供应的整合者,康美算是第一个成功地把互联网里的“平台效应”应用到中药材贸易中去,大幅提高了中药行业上下游衔接效率。要是没有后来的财务造假,可能如今医药龙头队列里也会有它一个位子。
当然,在中国的医药行业里还有两家巨头,是一个特殊的存在,一个是片仔癀,另一个就是云南白药。“国家保密配方”决定了它们的产品能够长期享受到市场独占的红利,也能让其围绕旗下的核心品牌做各种延申。
其中,相比片仔癀更偏保健品属性,云南白药有着自己一套完整的药材种植、中药开发以及产品销售体系。独家产品给到它良好的竞争力,业务规模赋予其抵御风险的能力。因此,在过去十年里各种新老面孔你方唱罢我登场、整个医药市值排名大洗牌之后,云南白药也是为数不多的长期排在前列的制药公司之一。
而如今,行业慢慢走向正轨之后,居民消费水平开始升到一个新的台阶,同时老龄化的趋势带来的高发病率之下,群众不再满足于“有药可医”,而是如何医得更好,更便宜,用中国的人均消费就能享受到全球最顶级的医药救治水平。
时代需要的是各家企业认认真真、踏踏实实的把转化、临床做好,在有药的基础上做到更进一步,满足更多、更好、颗粒度更细的临床需求。也就是如今老生常谈的“创新”。
2、创新年代下的自救
2014年,医药行业突然停下高达20%以上的增长速度,逐渐回落至13%至15%。
慢不是目的,为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腾挪出更多的空间和资金才是。
2014年起国家相关政策出现变化,利好创新药的政策密集落地。比如,改革药品器械审评审批制度,出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、药品上市许可制度,设立突破性治疗药物、附条件批准、优先审评审批和特别审批四条“快速通道”,加入ICH融入国际化等。
在资本市场端,从港股18A和A股科创板,为未盈利的医药企业打通了上市融资的渠道。
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,激发了我国医药企业创新热情。此消彼长,传统药企“大品种、重营销、轻研发”的固有模式逐步打破。以带量采购为代表的医保控费改革,更是持续挤压仿制&成熟药的市场空间,倒逼传统医药企业转型升级。
在这个过程中,虽然各家大厂都有着自己一定的应对方式,比如有的靠着独家品种豁免控费政策,有的尝试引入泛健康产品来对冲既往药品销量的下滑,还有的则往上下游拓展,从供应链上去赋能自己的医药工业。
然而,在“创新”这一时代的主旋律之下,传统药企的转型创新口号仍旧是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。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,一些大药企对既往的经营模式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庇护心理,对创新不坚决,导致转型多年归来依然是销售型企业。
2019年,国产IND(新药上市申请)数量达到235个,其中创新型Biotech公司合计申报163项IND,占比达69%;传统药企只有30%。在走上研发驱动型的道路上,传统药企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。
即便有转型的决心,大型药企受限于层层审批的流程制度,一线和决策层之间的环节漫长,运行效率势必降低,离市场也很远。
传统药企逐渐看清事实——既有业务体量太大,转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,创新又是一个长周期和高投入的过程。于是,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共存的模式,由传统业务作为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营收来源,创新业务贡献美好的预期和弹性。
在创新业务的探索上,一些大药企不免想走些捷径,比如扎堆在TNF-α、CD20、HER2、VEGF等已然热门的靶点。毕竟这些靶点已经有标杆产品作为参考,成药风险不大。但大家似乎都不愿意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,如果在热门靶点的追逐赛中,跑到第五名开外,那么再厉害的销售能力都难以挽回的。
还比如,很多公司想减少研发时间和建立的团队成本,直接挖团队,甚至疯狂“买买买”,通过收购创新药和创新器械企业快速布局。收购本身是普遍的商业行为,问题是大多数企业很难有足够前瞻的眼光和运气
十年过去,创新药收入占比超过仿制药收入占比的传统药企还没出现,反而各有各的苦恼,轻则和十余家企业抢一块地盘,重则十年没有创新产品上市、建设多年的制药基地无法投产。
当“捷径”成为弯路,也给传统药企提了个醒:生物医药不存在弯道超车。
3、从“基础”打起
弯道能超车,也容易翻车。中国创新药这一波泡沫堆积再破灭的过程,给整个行业留下一个教训就是无论在弯道超车还是在直道追赶,一个前提就是,要先把基础打牢。
还是拿云南白药来讲。
相比于生物药和化学药的创新药,中药创新药处于劣势,中药企业能守住市场身位很不容易。中药也在谈转型,但中药有舍弃不开的“根”与“传统”,从何转型是个问题。云南白药也有一脉相承的根本——白药。
没办法在“保密中药成分”上去做大/小分子上的创新延申,云南白药的转型就从回归基础研发开始。云南白药中央研究院下设云南省药物研究所,聚焦中药、民族药等天然药物的资源、药理、毒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,探索厘清其作用机理,做好中药研发的第一步。
云南白药的发展思路也改了,从过去依托产品发展变成用平台化思想,向外取经。
公司与十所高校开展合作,涉及肿瘤、自免(包括皮肤等)、骨科等赛道。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每年接收云南中医药大学、昆明医科大学等代培研究生10余人、实习生上100人,形成了良好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关系。而除此之外,云南白药干的更大的一票,就是找到了北大。
云南白药和北京大学早在2018年7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,2019年合作设立北大-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。北大-白药医学中心尤其重视临床,又有很强的人才优势,第一批引进的8位资深研究员中有三位院士,还有15位北大PI进入项目团队。
顶级的学府背后是高密度科研创新资源的投入。如今北大-白药医学中心正在肿瘤学、生殖医学、创伤骨科等多种领域开展合作,走向更前沿、更基础的理论中去,并促进基础研究应用于临床。
云南白药中央研究院的下设机构,除了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和北大-白药医学中心,还有创新药物中心。核心研发团队囊括了从科研到临床,从化药、生物药到核药方面的海内外人才,形成完备的科研、转化、临床的开发体系。
如此投入下,目前公司也有若干可圈可点的成果出炉。
比如,全三七片是中药注册分类改革后云南白药首个获批临床的中药1类新药。其用于心脉瘀阻所致的胸闷心痛等的临床试验已经进入II期。据悉,全三七片有望在2024年完成III期临床研究,同步完成药学相关研究,形成商业化生产工艺和质控体系,预计2025年向NMPA进行生产注册申报。
云南白药亦瞄准了核药这一赛道。
核药即放射性药物,主要应用于心血管、中枢神经系统诊断,骨关节类、血液疾病、免疫性疾病及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领域。这是一种转型的新思路——通过布局以核药为中心的创新疗法,打造精准诊疗创新方案,以带动公司创新药板块的发展。
云南白药特地设立全资控股子公司云核医药(天津)有限公司,重点研究核药。公司引进北京大学核医学科副主任杨兴教授,以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教授等专家研究成果,同时与国家有关部门、研究机构等形成战略合作,在核药产业链上、中、下游皆有布局。
目前已启动的核药项目为INR101和INR102,据云南白药2022年年报,INR101创新药项目是一种用于前列腺癌诊断的创新核药,具有高特异性、低非靶器官蓄积等特点,更有利于原位和局限期前列腺癌的诊断和治疗。
生物创新药,如今低垂的果实难摘了,革命性的结果短期内不容易看到,能做的就是在过程中做到尽善尽美,用十二分的投入去脚踏实地的做好一件事。先打好创新的基础。
创新药的基础有两层含义:一方面是完备的科研、转化、临床的开发体系;另一方面是要走向更前沿,更基础的理论中去,才能提前挖掘的别人挖不到的结果。
这是云南白药这家老牌中药巨头,尝试在创新的年代里去做的一些转型。
4、尾声
2023年11月4日,来自北大、海军军医大学、中国药学会以及其它一流医疗机构/高校的教授们齐聚无锡,探讨中药新型药物递送系统的技术发展。
这是云南白药在研发驱动,构建开放平台,加快推动产业创新战略上再迈进的一步。